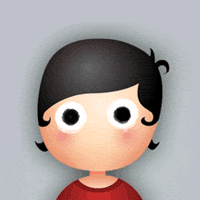纨绔姐妹
房间走廊的另一边是一个都弥漫着木头的香味,书橱的香味。书橱是二十四个梨木格拼凑而成。没有任何加工的原木书橱,除了放书,还有书格里放着酒,各种精美的酒瓶,酒瓶未开启就已经闻到了酒香。书格里还放着古玩店里淘来的笔筒、瓷瓶、精美茶具、罐子、钟表、外文画册、铜铃、咖啡壶、达利的抽象画、阿姨和一个男人的合影照片。放置的书都是些大部头的著作,十九世纪的英法小说,曾氏杂钞,西方作家的传记。一个巨型书桌,巨型瓦罐台灯,闪烁着紫油光的桌面,上面摆着两个瓷罐,却没有电脑。西式座椅,像是很久没有人坐了。窗户前摆着一张木质大床,上面只有两个靠垫,能看见阳光照在木质床头的花纹里,金黄色的一个平面。白色的窗棂,米黄色的窗帘,有两个瓷瓶里插着枯萎的花,所有的花都已经死了,却还插在瓷瓶里,散发出香味,奇怪的是,那种香味却是永恒的。岁月也无法改变它。这显然是一个男主人的书房,却好像已经永久没有在这张椅子上坐了。
上了二楼,阿姨正在举杯往喉咙里灌液体,起初我以为她喝的是什么饮料,后来才知道是红酒,她说她在跳舞之前总要喝一点酒,她说少量的饮酒会使舞姿更优美。阿姨在舞池里跳了起来,一个身轻如燕的女人,我都没有发现她什么时候已经换上了一件黑色丝绸舞服,一双红白相间绣花舞鞋。阿姨跳的舞是我从未见过的,反传统,技巧趋于自由形式,有抽象派的特色,又有表现主义特征。一个看起来平庸的女人,跳起舞来却很有品位。
离开她家时,我又回头看了看那扇窗户,向爬在窗台上吹风的老阿姨挥了挥手。
父亲忙着把一块木头雕刻成一个烟斗,他之前雕刻了一个,却没有成功,这块木头是外地的一个书商寄给他的,他在上个星期五才收到。他总是乐于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
“我要学跳舞,”我郑重其事的告诉父亲,“从星期一晚上开始,我要跟苏西阿姨学跳舞。”
“跳吧,跳吧。”父亲一边做手里的活,“带着你妹妹一块跳,让苏西编一支双胞胎姐妹跳的舞,搞一个组合,就叫“纨绔组合”,没准还会跳出名气来,去舞林大会获得名次,给你父亲脸上添光。”
我知道父亲会爽快答应的,只要是跟苏西在一块的事,他都同意,他喜欢苏西这个人,喜欢这个看起来很刁钻,却充满了感性和灵性,又非常有艺术气质,有品位的女人。
贸易公司把整栋楼的保洁都承包给了母亲,她雇了一些家政公司的妇女,那些妇女来自乡下的那些村镇,很能吃苦,干起活来特别卖力。她当了经理,她有独立的办公室,她居然穿上了新的制服,跟上个月比起来显得有些雍容华贵,端庄大气。她居然当上老板了,她每天勤勤恳恳工作就是为了能有今天。
星期一晚上,我急匆匆的赶往苏西的家,门口有几个孩子等在那里,我跟她们一块儿等,等到七点钟,门才开了。依然是那个老人开的门。我迫不及待的上了二楼,我找到了那个孩子,他仍旧身处一个小的乐园里,一个非洲的原始丛林。我抱起他,他睁大眼睛看着我,看着我陌生的面孔。他没有哭,也没有闹。还用小手在我的眉毛上拧了一下,我有疼痛感,疼痛让我倍加喜欢他。是什么人在我身后用双手蒙住了我的眼睛。这一惊吓,我差点把孩子扔在了地板上。手的香味让我猜出了她,是苏西,是阿姨。
连同我,一共有六个女孩。子绔没有来,她正在会计学习班培训。那个学习班也是在晚上上课。她要完成培训才能在母亲给她找到的那家企业上班。
,那五个孩子已经学了很长时间了。我属于初学者。我站在一旁看着她们跳。我才注意到五个孩子其中的一个,她的腿不是很灵便,有点蹩脚的感觉。苏西在纠正她们的动作,一边还用手比划着。让我吃惊的是,另外四个女孩竟然是聋哑人,她们的舞姿却很优美。尽管我看到的舞姿很美可我的心一点都不能平静。这些孩子到底来自哪里?为什么都是残疾女孩?还有,苏西的男人怎么没有回来,来他家两次,那个男人都没有露面,那样酷的一个书房,竟然没有主人。第一次来苏西家的那天,我还摸到了那个书房桌子上的灰尘。跳舞的女孩都很安静,让我一点都不习惯,我甚至打消了我在这里学习舞蹈的念头。我至少要在这里待上一年,融入到这些特殊群体中,想跟那些一块跳舞的孩子说上几句话都成了奢望。只能微笑着面对苏西,跟她交流,跟她探讨,她有花一样绽放的笑容,身段像春天发出新芽的小树。
两个小时后,舞蹈结束了。在院子里停了好几辆车,都是来接孩子的,只有我一个人要坐很长时间的公交回家。那些车里的窗户上都贴着膜,看不清里面开车的人。那几个孩子一个个上了车,有一辆车的司机还下来给那个孩子开了车门。我没有看清司机的脸,只看见她飘逸的长发,穿一件灰色的长风衣。她上了车,车消失在凝重的夜色里。
苏西摸了摸我的头,她看着我的眼神,说:“好好跳舞,没必要知道她们的来历。”她把我送到附近的公交车站,等我上了车,她才转身回去。
苏西一面经营她的音像店,一面教那些孩子跳舞。每天下午,当店门关闭后。苏西急匆匆的赶回家,做饭的老阿姨早就将晚饭放在那个菱形的桌子上。她来不及看一下孩子,就狼吞虎咽的吃完那些饭菜,老阿姨是苏西娘家来的,在她家已经干了很长时间了。做菜的手艺不错,苏西也不是那种挑剔的人,饭菜很少有不合口的时候。我每天去跳舞都要先上楼抱一抱那个孩子,好像她是我的亲弟弟。他抱在怀里感觉越来越重,没有见这个孩子哭过。他很顽皮,有的玩具已经被他损坏了。在通向楼梯口的一瞬间,我看见了一个人影闪进了楼下的那个书房,也许是幻觉,每次去苏西家,我的心里都会想着,那个书房的桌子后面会不会坐着一个人,一个文质彬彬带眼镜的心理学博士。我想问问老阿姨,那个书房的主人的事,可我怎么说呢。我实在是想知道书房的主人的事。那么漂亮的一个房间,如果没有主人,那将太可惜了。我用手擦了擦眼镜,我看错了吗?不过,我的确看见了一个人影闪进书房,人影进去的速度非常快。我轻轻的推开门,屋里暗的让你害怕,房间的窗帘是拉着的,只有墙上的白色的照片发出昏暗的光。没有一点声音,我的听觉和视觉都已经凝固了,只有一颗勇敢的砰砰跳动的心。我探着步子向里走,才走了几步,就有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你在干嘛?”
啊!啊!我惊叹道。我看见老阿姨后,差点没有晕了过去。她打开灯,什么也没有看到,整个房间的色调是我第一次进来时看到的一模一样。窗边多了一个花瓶,瓶里插着一个绿色图案的旗子。一会儿才缓过神,我告诉阿姨,我只是想进去看看那些摆在书柜里的小工艺品。走到院子里,我惊恐的心还太跳动。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家,我和苏西在那张温暖的大床上度过一夜,阿姨的身体是我见过的最美的身体,白的像牛奶一样的身体。她的身上有一种自然生发出来的香味,不是香水的气味,是皮肤毛孔生发的香味。她喜欢裸睡,睡得那样深、那样沉,像婴儿的睡眠。我似睡非睡,我还想着闪进书房的那个人影,他会不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上到二楼来,我打开灯,看着天花板上的莲花吊灯,映衬着窗外璀璨的霓虹。白天的恐惧在夜晚继续延续。我想问苏西一些关于书房的事,看她睡得那样沉。也无心打扰她,我睡着时天已经亮了。
星期天,父亲要约朋友办事,让我给他看会书店。店里的客人很少,一个驼背的戴眼镜的老人走进书店,他的腋下夹着一个帆布袋子,他说他要买一包烟,我告诉他这是书店,旁边的店里有烟买,他听不清,我又重复了三遍,他才缓慢地转过身走出书店。
没有客人,听到了猫的叫声,微弱的猫的叫声。不知是从哪里传来的猫的叫声。我顺着声音寻找,叫声是从墙壁里传来的。在两组书柜之间,有一个碎花条形布帘挂在《第三帝国的兴亡》和《国富论》之间狭小的空间里,就在这个缝隙里,我发现了一个暗室。天哪,父亲居然也有这样大的一个秘密。只能挤进一个人的身躯的一个缝隙。进去是一个走廊,有一点可供行走的光,猫从我的脚下窜出去,跑进书店,从正门溜走了。我把书店的门从里面锁上,父亲暂时不会回来,我翻身挤进通向暗室的走廊,我发现了一个比书店还大的会客厅,里面有一组沙发,茶几上放着一个木制烟缸,一些烟斗和烟丝放在上面。一个可供十个人用餐的桌子,桌子中间有一个藤编花篮,花篮里放着没有香味的假花。一面墙上有三幅画像:、西蒙·波伏娃和苏珊·桑塔格。西方知识女性柔美的冷色调的油画。开始,我并没有认出这三个人,画的下面都有她们的名字。另一面墙上挂着几幅音乐家的画像:肖邦、德彪西、小泽征二、李斯特。桌子上没有餐具,房间的拐角有一个小门,里面是一个厨房,各种灶具一应俱全。再向里走,便看见一个仓库摸样的房间,里面放着一些没有拆封的书,和一些旧报纸。帘子后面有一个木床。上面的被子没有叠,床单还散发着一种奇香,像是百合和栀子的混合味。床上放着一本扣着的《马语者》,掀开后墙的窗帘,便看见院子里有一栋昏暗的旧楼房,是一个老年人才居住的老旧小区。从阳台上能看见老年人晾晒的深颜色的衣服。后门被一个立柜堵死了,很久没有从后门进出了。我把父亲的秘密装在心里,返回到书店,开了门,坐在收银台后面的椅子里假装看书,快到中午十二点了,父亲才回来。他从袋子里拿出几个冰糖葫芦,算是给我的犒赏。我走出书店,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走到一棵槐树下面,我又返回书店。“爸,如果再需要看店的话,我愿意效劳。”
关于苏西家的书房,关于父亲书店里的暗室,给我幼小的童年留下了神秘的色彩。那种好奇心、那种压抑的心灵的结点。总想去探究,总想去追问。你没有勇气打探。还不能把这个秘密告诉母亲,他们的感情本来就不好,你不能雪上加霜,你只能慢慢的等候,等候那些神秘的房子里到底会发生什么神秘的事情。
父亲的威严和多面性,他与母亲之间的关系,那种不说话,不畅谈,只吵架的关系,会伤害我吗?当然伤害的不轻。你要学会习惯,学会适应。即使打起架来给你造成的恐惧就更不用说了,那种恐惧是刻骨铭心的,你恨不得找一个地洞钻进去。母亲,她对我们姐妹俩是不屑一顾的。但是,有时也会心血来潮带你到很远的地方去玩,去之前也不告诉父亲,手机都是关着的。我们坐在母亲的那辆破旧的福特T型车上飞奔,在一条灰色的笔直的马路上,呼呼闪过的是那些枯萎的树,路边的牧人在挥舞着鞭子吆喝那些羊群,你身处一个亮丽清新的世界。“开慢一点,妈妈,我害怕!”子绔说。车速慢了下来,被带到山脚下的雪地里,下车后三个人不停的奔跑,观赏那些裸露的冰冷的岩石,混沌的灰蒙蒙的天。你的鞋里钻进雪了,她也不在意,厚实的棉衣穿在母亲身上,你会看见她臃肿的后背,那条围巾很久没有换过了,她是那样怀旧的一个女人,一头卷发上飘着雪花。就像在马场看见的马头上的雪。脸是红色的,那种苍白中透出的红色。看见野兔在雪地里奔跑留下的脚印,干枯的树上挂着彩色的丝巾。尽管很冷,你却喜欢,喜欢雪的纯净,喜欢山谷的空灵,喜欢纯净的雪发出的光。步行到山谷的另一边,看见农舍门口的招牌,那种对外营业的农家小饭馆。有温暖的炕、烧煤的炉子、香喷喷的羊肉。进了温暖的屋子,你才感觉到脚的冰冷,母亲把她两个女儿湿透了的鞋放在炉边的石凳上烤。被火烤过的鞋穿在脚上很不舒服。要吃一顿以羊肉为主题菜的大餐。我们看见几件冷兵器摆在屋里的墙角:矛、叉、戟。农舍的主人说,夜里有几只狼会来敲门。那些兵器就是对付夜里来骚扰的狼。他的话让你闻到了狼皮的味道,闻到了血腥味。我们也联想到了那些锅里炖的岩羊的肉,他会不会猎杀他们。尽管很饿,却已经没有了胃口。
农舍主人把我们送过山谷,他才回去,她的夫人还站在门口迎接他。就两个人,夜里狼来了可怎么对付。女孩总是对什么都担心,你要关注那些奇奇怪怪的事。几天后,你会在母亲跟前嚷着要再来山里看看,看看他们是不是还活着。
自从发现了那个暗室,我才知道猫为什么经常光顾书店,它不是那种求知欲很强的动物,那些书跟猫毫无关系,它只是为了溜进暗室的厨房里,偷吃头一天晚上剩下的饭菜。一条饥饿难耐的流浪猫,有时,它溜进暗室,父亲是不会发觉的,即使它发出叫声,父亲也听不见。猫把暗室看做是它的天堂。城市带给动物的食物非常匮乏,猫是从不在垃圾箱觅食的。猫非常干净,也非常注意名节,它宁可饿着,也不吃那些它认为不清洁的东西。每次,它走到书店门口,目光透过玻璃门,看看父亲的神态,看看他是不是睡着了,看看书店里的客人是不是很多。即使被父亲发现了,也认为是买书的客人带来的宠物。猫迈着小碎步,托着矫健的身躯,跟着一个穿裙子的女孩进了书店的门,从客人的脚下穿过,在书店的地板上打个滚。步入《第三帝国的兴亡》和《国富论》之间的狭小区间里,闪身进入暗室。用灵巧的嘴轻轻吹一声口哨,在肖邦和德彪西的眼皮下面,毫不费事的进入厨房,那里摆着头天晚上吃剩下的三文鱼刺身、腊肠、基围虾、鱼头豆腐汤。它必须在厨师到来之前将肚子填饱。猫的胃太有限了,最近“血糖”有点高,“血压”也不正常。它必须保持正常的卡洛里的摄入。它看了看墙上精美的挂钟,时间还早,它就在仓库地板的垫子上睡了一觉,多么酣畅淋漓的一个觉。父亲正在书店的收银台数钱,他万万没有想到,猫在暗室里进行了一场浩劫。
后来发生的事可想而知,父亲跟苏西生活在了一块,在法庭上,法官问,子纨、子绔,爸爸和妈妈你们跟谁?我们犹豫了一会,法官让爸爸妈妈先出去,法官看着我,意思是让我先说……
我现在是舞蹈学院的一名学生,不过,将来毕业了我也不想结婚,像艾米丽·狄金森那样独身一辈子。
作者简介:李正果,本名李勇,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宁夏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长篇小说:《阿拉斯加少女》、《栖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