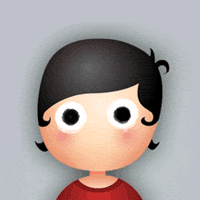摘要:汉墓出土蟾蜍灯具寓意可分为两类:一类为祥瑞符号,包括蟾蜍与兔子结合构成月亮意象,或单独蟾蜍构成“万岁蟾蜍”祥瑞动物形象;一类为寓意登仙和长生不死,由蟾蜍与乌龟结合构成西王母神话的一部分。蟾蜍频繁出现于灯具之上,体现了汉代“德化瑞应”思想和神仙信仰的普及。
蟾蜍是汉代图像和造型艺术的重要内容,以往对于蟾蜍寓意的研究多从汉画着手,因为有着复杂但明确的构图,兼以相对清晰的文献记载,蟾蜍的寓意并无太多争议。[1]但是作为造型艺术,因其实用功能,构型相对单一,而且汉代的模型明器造型多被认为是单纯的写实动物,因此灯具上的蟾蜍是否具有象征意义?能否将汉画中蟾蜍的内涵简单扩展到造型艺术之中?则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目前已知的汉墓出土的具有蟾蜍形象的灯具共7件,分别为:河南济源泗涧沟汉墓1件,四川雅安小山子岩汉墓1件,江苏盱眙大云山一号汉墓2件,重庆巫山麦沱墓地1件,四川成都跃进村汉墓1件,四川博物院馆藏1件。7件之中,除大云山一号汉墓的2件灯具为青铜外,其余均为陶制。
这批灯具的蟾蜍造型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包括泗涧沟汉墓陶灯、小山子岩汉墓陶灯、大云山一号汉墓铜灯和麦沱墓地陶灯的蟾蜍,作为灯具底座出现;第二组,包括跃进村汉墓陶灯和四川博物院馆藏陶灯的蟾蜍则是作为灯柱出现,承托灯盘,底座为龟。两组灯具蟾蜍结构上的差别,显示着内涵上的不同。
一、祥瑞符号:月亮与万岁蟾蜍
第一组灯具中的陶灯蟾蜍又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蟾蜍与兔子的复合结构。河南济源泗涧沟蟾蜍座陶灯(M24∶9),出土于一座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的墓葬之中。陶灯基座为蟾蜍形,灯柱上部为兔形,灯盏为昂首、振翅、翘尾的鸟形,灯盘中心有一锥状火主。陶灯通高27.8厘米。除灯盘内涂红褐色釉外,陶灯均涂较薄的绿色釉。简报执笔者认为,陶灯鸟形灯盘和汉代画像石上的金鸟含意相同,象征太阳,中柱和灯座塑兔和蟾蜍象征月亮;整件陶灯日月相合为“明”,并引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拓片金乌图形和“大常明”铭文,认为昼有日,夜有月,意为常明。这样的艺术造型是象征灯明之意(图一)。[2]后来,孙机肯定其造型寓意为“明”的同时,认为鸟形灯盏可代表阳燧,陶灯为“明烛”之俦。[3]事实上,简报援引《贞松堂集古遗文》的“大常明”行灯铭文,位于灯盏外底部,铭文旁仅有金乌形象,未见代表月亮的蟾蜍和玉兔形象。因此,“大常明”铭文仅与代表“日”的金乌相关,而与日月相合为“明”不存在必然联系。汉魏时期,“明”字多从“目”从“月”,其中“目”为“囧”之衍,表示窗牖。极少作“日”的情况下,“日”亦应为“目”的简写。[4]因此,“明”字在语源上,不是日月相合,而另有渊源。不过,不能否认灯具在造型上,日月同构具有表示光明的意思,汉魏铜镜常有“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吾作明竟世少有,明如日月,……”、“与君无极毕长生,如日月光芒”的铭文,以日月表示光明。或认为此件陶灯表示日月合璧或日月同辉的吉祥天象。
图一 河南济源泗涧沟汉墓出土蟾蜍座陶灯(M24∶9)
四川雅安小山子岩墓陶灯,灯柱为一兔和一蟾蜍的合成体,兔的两前肢高举并托着盏底,后两肢骑于蟾蜍颈上,蟾蜍前肢弯屈为伏状。[5]2件灯具主体造型都是蟾蜍与兔子的组合,明确标示其为月亮的意像;灯盘做成鸟状或圆盘状,可能标示太阳的意像,以日月相合象征光明与吉祥。
另外一类灯具为单纯的蟾蜍造型。2009年,江苏盱眙大云山一号墓发现2件青铜五枝灯。其中1件(M1∶3707)有灯枝五枝,上饰竹节纹,每枝顶头套一灯盘。灯座为蟾蜍形,蟾蜍身扁平,四足蹲踞,头部饰两角,背部正中设一銎以承灯枝。盘径9.3、盘深2.5、通高60.8厘米(图二、三)。另1件(M1∶3708)的形制、尺寸、纹饰基本同上面提到的五枝灯,仅在蟾蜍尾部有一突出的尾巴。[6]此处头上长角的蟾蜍在汉代造像和图画中极少发现,此前在四川大邑县董场乡画像砖墓曾有发现。[7]南京博物院1件东汉鎏金镶嵌兽形铜砚盒,其兽形为带长角的蟾蜍状。[8]此蟾蜍应是晋葛洪《抱朴子·仙药》中记述的标准“万岁蟾蜍”形象,“万岁蟾蜍,头上有角,颔下有丹书八字再重,以五月五日日中时取之,阴干百日,以其左足画地,即为流水,带其左手于身,辟五兵,若敌人射己者,矢皆反还自向也。”[9]而蟾蜍背上的五枝灯则象征万岁蟾蜍背上生出的“芝草”,按《渊鉴类函》引《道书》记:“蟾蜍万岁,背生芝草。出为世之祥瑞。”[10]则整个蟾蜍座铜五枝灯塑造的就是一幅“万岁蟾蜍”瑞象图。1999年,重庆巫山麦沱墓地出土1件釉陶灯(M47∶47),由圆形灯盘、圆柱形灯柱和蟾蜍形灯座三部分组成,方底座中空直达盏底,灯盘浅斜壁平底,中心突起一烛钎。陶灯口径13、高21.8厘米(图四)。[11]这件陶灯亦应归入此类。
图二 江苏盱眙大云山一号墓出土青铜五枝灯(M1∶3707)
图三 江苏盱眙大云山一号墓出土青铜五枝灯(M1∶3707)局部
图四 重庆巫山麦沱墓地出土釉陶灯(M47∶47)
汉墓出土灯具造型的此类蟾蜍寓意,蟾蜍与兔子结合构成月亮的意像,或单独蟾蜍构成“万岁蟾蜍”的祥瑞内容,是汉代祥瑞观念的形象表达。汉代“天人感应”、“祥瑞”之说盛行,当时人认为上天是有感情的,时刻关注着人间诸事,通过“天垂象”表达其对世事的好恶之情,通过“见(现)吉凶”奖掖或惩罚世人。人们则希望自己的德行符合“天道”,而能“邀天之福”,并且逐渐总结构建起一整套规范的“德化瑞应”体系。《白虎通义·封禅篇》:
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者,以为王者承天顺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德及天,即斗极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即嘉禾生,蓂荚起;德至鸟兽,即凤凰翔,鸾鸟舞,麒麟臻,狐九尾,雉白首,白鹿见;德至山陵,即景云出,芝实茂,陵出黑丹,山出器车,泽出神马;德至渊泉,即黄龙见,醴泉涌,河出龙图,洛出龟书,江出大贝,海出名珠;德至八方,即祥风至,钟律调,四夷化,越裳来,孝道至。[12]
在这样一种思想观念下,人们祈愿符瑞能来,能现,尝试各种方法努力达到“德及万物八方”的境界。相应地,人们在壁画、织锦、帛画上刻画寓意吉祥的图案以昭示使用者、拥有者的德行,希望受天的福佑,祈求自己平安、吉祥、幸福。祥瑞内容并不单以图像形式存在于帛画、织锦、画像、铜镜之上,也以塑像的形式存在于灯具、博山炉、乐器底座等日常生活用具之上,以此将“德化瑞应”思想渗透进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灯具上塑造寓意月亮和万岁蟾蜍等瑞象的蟾蜍,即源于此。
二、登仙与长生不死:西王母的神仙世界
除了祥瑞寓意外,还有一类灯具造型的蟾蜍,以蟾蜍蹲踞在乌龟之上作为造型主体,则另有寓意。类似灯具有四川成都跃进村汉墓出土陶灯和四川博物院藏龟蟾座陶灯。[13]其中,成都跃进村汉墓陶灯为解开此类造型的象征意义提供了线索。陶灯底部为一龟,龟颈背相交处为双臂伸展擎举双盏的猴子形象;龟背上立一蟾蜍,阔嘴张目,头顶灯盘;蟾蜍背上塑一斗拱,斗拱中间浅浮雕西王母图像;西王母拱手拢袖,端坐于双头兽座之上,头上有三足乌,身下有九尾狐,左右两侧各有一人蹲坐在兽头之上;斗拱上部为灯盘。通高60厘米(图五)。在西王母主题的各类汉代画像题材中,蟾蜍通常绘制在西王母身边,以西王母仆从身份,与九尾狐、三足乌、捣药兔,有时还包括猴子等,共同构成西王母神话体系图。此件陶灯的蟾蜍虽然体量较其他动物大,但仍应该为西王母的从属,是构成西王母神仙体系的一部分,陶灯所营造的就是时人心向往之的西王母的神仙世界。
图五 成都跃进村汉墓出土陶灯
至于蟾蜍下面的乌龟,则可能是西王母所居的昆仑山、龟台或龟山的形象表达。魏晋六朝人杂采《山海经》《穆天子传》《汉武故事》及一些道教传说,并伪托汉桓驎撰《西王母传》中载“西王母者,九灵太庙龟山金母也,一号太虚九光龟台金母元君”。西王母“所居宫阙在龟山,春山,西那之都、昆仑之圃、阆风之苑。……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涛万丈,非觚车羽轮不可到也”。[14]既然西王母宫苑所在即名龟山、龟台,又有“弱水九重,洪涛万丈”,那么,将龟山塑造为乌龟的样子自然就符合当时人们的理解与认识。应该说明的是,龟山在六朝上清派经典《龟山玄箓》卷上为“西龟之山,一曰龙山,乃九天之根纽,万气之渊府”。[15]说明龟山也叫龙山,而且龟龙习性相近,都是喜水的神兽,甚至是“一而二,二而一”关系。部分画像石和塑像中西王母也是乘龙的,陕西绥德王德元墓门的西王母东王公的画像下方,蛇龟纠缠的神兽,似乎既可以理解为方位神玄武,也可以理解为西王母所居龟山的写照。[16]
将龟山、龟台塑造成乌龟的形式,是把比较复杂的西王母神话进行简化处理,主要出于灯具便于移动的实用功能的考虑。类似这种将西王母神话体系简化后塑造成实用灯具的情况,亦见于济源泗涧沟汉墓的2件桃都树的陶灯。[17]四川博物院藏龟蟾座陶灯,蟾蜍背部有大孔,其上应还有其他构件,可能为同类西王母主题陶灯,但是仅存龟形灯座和蟾蜍形灯柱底部(图六)。
图六 四川博物院藏龟蟾座陶灯
这一类灯具上塑造蟾蜍,不同于前者的祥瑞寓意,它是西王母神话体系的一部分。西王母神话随着时代地域的变迁,不同等级阶层往往赋予其不同意义。目前发现的此类灯具均集中出土于东汉时期的四川地区,是当时四川西王母崇拜盛行的表征。此类西王母神话还普遍见于当地摇钱树、石棺、画像砖、铜镜、陶俑之上。把西王母神话构成要素的蟾蜍,塑形在灯具之上,寄托了东汉时期生活在四川地区的人们希冀登仙、长生不老的美好愿望。
三、结语
蟾蜍作为神仙信仰的重要构成要素,在汉代图像作品中常见,并且因为有着明确的情景依托,其内涵十分明确。而在世俗生活使用的灯具上,汉代,特别是东汉以来,人们往往倾向于以动物或人偶进行塑形装饰。而作为灯具造型装饰的蟾蜍,尽管缺乏必要的情景依托,往往单独或与其他动物共同搭配,并未改变其特定寓意———万岁蟾蜍、月亮意象、西王母的神仙世界,并未因装饰灯具而随之丧失其在神话体系中的意义。[18]蟾蜍出现于作为日常生活用品的灯具之上,虽然数量不多,仅零星见于贵族大墓或一般的平民墓葬之中,既有造型简单朴素的单枝陶灯,也有比较复杂精致的多枝铜灯,但这也反映出汉代神仙观念和信仰向民间普及,向世俗转化的特征。
注释:
[1]郑先兴:《汉画像的社会学研究》,第262~273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2]河南省博物馆:《济源泗涧沟三座汉墓的发掘》,图六四川博物院藏龟蟾座陶灯《文物》1973年第2期。
[3]孙机:,第5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4]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第617~618页,中华书局,2014年。
[5]谢洪波:《论汉代巴蜀陶灯及其他地域文化信仰》,《求索》2012年第12期。
[6]余伟、盛之翰:《江苏地区出土汉代铜灯试析》,《东南文化》2014年第6期。
[7]胡亮:《大邑县董场乡残画像砖墓拾粹》,《成都文物》1990年第4期。
[8]尤振尧:《东汉鎏金镶嵌兽形铜盒砚》,南京博物馆博物院藏宝录编辑委员会编:《南京博物院藏宝录》,第174~17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
[9](晋)葛洪著,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校释》,第182页,中华书局,1980年。
[10](清)张英、王士祯等纂:《渊鉴类函》卷四四八“蛙”条,中国书店四库影印本,1985年。
[11]重庆市文化局等:《重庆巫山麦沱古墓群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2期。
[12](清)陈立著,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第283页,中华书局,1994年。
[13]苏奎:《成都跃进村汉墓出土陶灯的复原研究》,《文物》2015年第2期。
[14]段启明主编:《中国古典小说艺术鉴赏辞典》,第27~28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15]《道藏》第34册,第177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
[16]郑先兴:《汉画像的社会学研究》,第217页。
[17]胡成芳:《济源泗涧沟出土“百花灯”新解》,《中原文物》2007年第4期。
[18]苏奎《四川汉代西王母陶灯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17年第2期)一文,亦颇能说明神话意义的灯具装饰在汉代仍颇为流行。
(文章来源:《四川文物》2018年第2期)
作者:谭玉华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责编:岑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