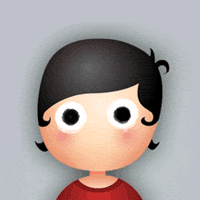她是扬言要将他吃干抹净的放恣女人,
恃美行凶明目张胆:“你关心我啊?”
于她,不过是逢场作戏,尽释光华另有其意,
而他,等待着她的獠牙毕现。
也如杯中鸩酒,
解我渴,又燎我心上莽原火。
剪风声惊鸿之作
美艳超模 vs 禁欲大亨
欲望都市里的心火燎原
“我对你,何止一句喜欢。”
爬到坡顶,队员们要滑下另一侧。
阿尔卑斯的山势很奇怪,百米落差中埋伏大大小小的蘑菇(雪堆),不易发觉,要滑到底下才能发现,无端就错过了。山坡遍布苍松,枝丫累累垂垂披雪覆霜,江鹤繁与瑞士导滑商定穿行树丛的具体滑行方向,一旁的何风晚调整动作,充满跃跃欲试的欢欣。
庞默走过她身后,抱怨:“你回来也没去看丛月姐。”
何风晚躲过他幽怨的眼神,笑得没心没肺:“我刚回去忙着找房子,兵荒马乱的,等过两天亲自登门赔罪。”
一分神,她绊了一跤摔倒在地。
因为没有套上雪杖腕带的习惯,雪杖抛远了,雪板也掉了,何风晚坐在雪地里挣扎,站不起来。
庞默好整以暇地欣赏她难得的丑态,遭到何风晚抗议:“帮帮忙好吧?”
他这才忍着笑,帮她拾起雪杖,把雪板斜插在雪地里。
找到雪板上的固定器后,庞默要帮何风晚除去雪鞋底部的积雪,但这一步要抱起她的脚。何风晚抗拒地缩了一下,说着“我自己来”,低头清理着。
麻利地穿上雪板站好,何风晚捕捉到江鹤繁来不及收回的目光。
她挪几步过去,仰头问:“你们商量好了吗?我都等不及了,什么时候开始滑?”
江鹤繁说:“他们开始了,我们就跟上。”
奇怪,为什么不能我们先开始?
何风晚满腹狐疑,可隔着护目镜,又看不出江鹤繁眼里的情绪。
她快忍不住了。
滑雪是会上瘾的,体会过飞翔的感觉,一辈子都无法戒断。
好在瑞士导滑很快冲下,庞默和同学紧跟其后。江鹤繁才刚滑出,何风晚已如离弦之箭“嗖”的一声从他身畔蹿出。
她握着雪杖,身轻似燕,灵巧地避开树丛,却也没跟着庞默那队,暗自拐向不知什么地方,须臾便没了影。
江鹤繁不得不赶紧跟上。
层层黑色的树影急速掠过,他盯着前方缩小的人影,突然闯入一大片纯白的空旷,先前的景色像遭抹平了一般。
平整的雪地上,何风晚俨然雪疯子附身,纵情划着弧线。前方再有十几米就是山崖,这是野地,没有任何标记,只有熟悉路线的熟手才能识出。
江鹤繁耳中一阵轰鸣,全速追去,冰凉空气渗出细小的锋芒刺激鼻腔。
何风晚似有警觉,开始减速。
江鹤繁不虞有此,差点从后撞上她。
何风晚一个急停,大叫:“你偷袭我?”
江鹤繁摘下护目镜,直视她,训斥道:“你再往前几米,就真该粉身碎骨了!”
“我知道的,我都减速了。”何风晚不齿,“这样的地形以前滑过。”
“别闹了。”江鹤繁眸色冷厉,“跟着我,是指不能超出我周围三米。”
“……”
“我让你滑,你再滑。”
何风晚不服气地翻翻白眼,还想说什么,江鹤繁已起步。
她只能跟上,问:“其他人呢?”
“走了。”
“不是说同路的吗?”
“我和那边导滑商量了一下,不同路了。”
“不打个招呼吗?要是他们发现我们不在了,会不会担心?”
江鹤繁减速,围着她绕一圈,用雪杖往某处一指,说:“你还能赶上,想去就去吧。”
说完,他便不再回头,纵杖滑远。
其实他早已打过招呼,说好他和何风晚从后绕去别的路线,不必惊动其他人。谁知她这么不识趣,他竟也有了怄气的心思。
她走了也好,或许他是该冷静一下。
但滑雪的簌簌声却从后传来,江鹤繁停住,一言不发地看着渐渐靠近的亮红色。
何风晚喘着大气,抗议:“你叫我不超过三米,自己又跑这么快!我怎么跟得上?!”
呼出的白雾罩住她年轻的面庞,又顷刻消散。
江鹤繁顿了顿,脱掉雪板,说:“我们爬一段。”
途中,他一脸冷淡神色,拒人千里。何风晚不满,再次抗议:“江先生,能不能笑一下?你这么严肃,我的好心情都被吓跑了。”
江鹤繁只当没听见,表情如遇冰封。
其实对于她跟来,他是有点开心的,有点松一口气的释然。
但他自小习得喜怒不形于色,暂时改不掉。
不过,两人的关系总算有所缓和。
越过嶙峋的山石,他们爬到山脊上。江鹤繁指向一处,说:“那是森林保护区,不准滑,我们要绕开。”扬手又指向另一处,说,“那片断层,是雪崩垮塌的痕迹,我们要小心些。”
何风晚不住地点头:“哦。”同时见缝插针地朝他猛盯一阵,腹诽他一定太吝于面部活动,才能迎着凛冽寒风也不见皮肤变糙。
跟着江鹤繁,何风晚滑过一片粉雪大坡,又从巨石上一跃而下,很是尽兴。
转眼便至午时。
江鹤繁带何风晚去缆车中转站休息,在避风处食用自带的三明治。
他脱掉头盔和护目镜,朗目清眉地端坐着,吃相泰然,何风晚看着他觉得一下顺眼许多。她身后的尾巴摇起来,拳头攥成话筒的形状,递去:“请问江先生滑雪和登山多久了?”
江鹤繁看着阳光投在地上的影子,不紧不慢地吞咽。当何风晚以为他不打算配合,有些偃旗息鼓地收手时,他突然说:“九年吧。”
何风晚的胃口又被吊起,继续问:“能了解一下你登山和滑雪的缘由吗?”
江鹤繁手上的动作一滞,神情变得凝重,说:“十年前,我认识一个人,他是我见过的最疯狂的登山者。他说,登山不是为了征服,是真切体会身为人类的渺小。”
何风晚随即敛起笑容,眼睛眯了眯,问:“原来有伯乐指引,那位伯乐与江先生现在还有联系吗?”
“没有了。”
“为什么不联系?”
“他已经……”江鹤繁微怔,眼里流露出困惑的神情,“何小姐问这个做什么?”
“哦,有点好奇啦!”何风晚眼梢一扬,脸上瞬间又洋溢起俏丽的风情,“就是觉得,江先生如今这么热衷,想必那位伯乐对你的影响很大了。”
江鹤繁放下三明治,往事兜头的沉重感袭来,但他没有表露,淡然地说:“谈不上热衷,养成习惯想戒掉不容易。他对我是很重要,我也对不起他,答应帮他找的人,至今没找到。”
“那是什么样的人?”
这一次,江鹤繁没再回答。
何风晚一连串的追问,已经超过他心中好奇的标准,变得可疑。
几下解决了三明治,江鹤繁起身,说:“一刻钟后出发。”
何风晚横他一眼。
小气!
两人坐缆车转至海拔三千米处,江鹤繁指着前方的长坡,说:“翻过那个山垭口,滑下去。”
何风晚眼里满是蠢蠢欲动的兴奋,欢呼:“好!”
天空飘浮着絮状的闲云,苍凉又寂寥,蓝得旷古绝伦。
极目之处皆是蔽天的白,风声时作时辍,拂去世上一切杂音。何风晚跟在江鹤繁身后,有些吃力地沿一公里的长坡跋涉。
翻越山垭口的雪坡时不能再用雪板了,七十度的坡面越发坚硬,要用冰镐挖出脚踩的浅坑。
照例是江鹤繁开路,何风晚跟在后面,惊叹轻柔的雪花经日照风吹的自然变化,积压出顽石的质地。
翻过约莫五层楼高的雪坡,视野随之开阔。他们爬到了海拔三千五百米处,远方是密密麻麻的峰峦,云遮雾罩,近处一壁空旷的斜坡赫然现于眼前。
江鹤繁戴好头盔和护目镜,转身叮嘱何风晚:“这一带都是新雪,危险性不知。你在这儿等着,我滑过去,你再滑。”
何风晚点头:“好!”
他随即出发。
身形俊逸潇洒,像白色大海上,一面抖擞的风帆。
然而滑出不过几秒,江鹤繁下方三十米处的雪坡裂开一道醒目的断层,他上方随即也出现,上下拼成一块不规则的四边形,整块区域轰然塌陷。
何风晚僵了僵,真的遇上雪崩了。
小时候和哥哥看电视里的雪崩镜头,何风晚曾为那样磅礴的气势震叹。
雪体剥离了附着的坡面,以摧毁一切的狂暴轰轰疾驰,似海面掀起的千顷巨浪,堆出浩渺烟涛。那是无数殉难者死前最后见到的画面,铺将在何风晚眼前,穷尽语言也道不出的壮丽。
可当她亲眼看见,壮丽荡然无存。
她只感到恐惧。
江鹤繁的身影缩小为视野中一个黑色的点,头顶便是奔涌而下的涛涛雪浪,随时都能将他吞噬。
何风晚腿软,双手撑住雪杖,扯着变调的嗓音大喊:“江鹤繁!快跑啊!快跑!”
凭仅存的理智,她拼命回忆欧洲雪崩规模的分级、长度和体积的裁定,估算眼前这场灾难的破坏性。于是,她眼睁睁地注视着那个黑色的点顷刻间没了影。
应该是场小雪崩,雪势还未抵达坡底就静了下来,全程不及一分钟。
但人没了就是没了。
何风晚彻底慌了神,支着雪杖滑去。
害怕见到江鹤繁遭雪深埋的惨况,但她仍全速前进,她还记得搜救步骤,必须争分夺秒。
慌乱中丢了护目镜,何风晚盯久了雪面,白亮反光刺激得眼泪落下,须臾风干在皮肤上留下细小尖锐的麻痒与疼痛,随后变成真哭。
“江鹤繁!”何风晚滑至雪崩发生的区域,双手合成喇叭,放声呼唤。
回应她的只有嘶号的风声,回忆印象中他最后出现的位置,何风晚立即按江鹤繁教她的方法搜救,从背包取出铲子挖雪。
不过最早教她搜救的,是哥哥。
那时何风晚才十岁,背过身去坚决不看,气鼓鼓地问:“你也知道有危险,为什么还去?”
哥哥布满粗茧的大手温柔地抚摸她的头顶,笑眯眯地说:“我没别的事情可做,只有这一件。我已经被征服了,凡是去过峰巅的人,都会一再地踏上朝拜的路。”
这真是太不浪漫的说辞,完全不能打动年幼的何风晚。
去国外登山不但费时费力,一次旅途就要付出几十万的开销,是何风晚清贫的家境不能承受的。武馆出身的哥哥后来不知结交了什么人,远赴非洲为私人安保公司工作,成为刀口舔血的雇佣兵。
毫不意外地死在那儿。
何风晚直到今天也无法理解,不止一次埋怨哥哥是个傻瓜,所有轻视生命的人都是傻瓜。
包括眼下不知埋在何处的江鹤繁。
“江鹤繁!你这个浑蛋!
“你要是敢死在这儿,我非扒了你的皮!
“我说到做到!还要放干你的血,剥光你的肉,让你就剩一堆骨头!
“呜呜呜……”
声音中混着断断续续的抽噎,何风晚气极,边骂边哭,害怕目睹江鹤繁被雪掩埋奄奄一息,又必须争分夺秒地找到他。她瞪着通红的双眼,脸上有了发狂的表情。跪倒在雪地上,她双手合力紧握雪铲,很快刨出坑。
雪质干硬,一点不比铲土轻松,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头顶上方蓦地传来一道低沉的男声:“挖的地方不对,我要是被埋了,该在你后面两米的位置。”
何风晚愕然抬头。
江鹤繁侧躺在一块岩石旁,周身被明亮的阳光勾出一圈温暖的毛边。
抹了把泪,何风晚手脚并用地往上爬了几步,生怕是自己出现幻觉,靠近了才终于看清他垂下眼睫,狭眸匿在阴影里,光线便跳上了颧骨和鼻梁,整张脸触目惊心的英俊。与他视线交会的一瞬,何风晚不争气地心跳隆隆。
江鹤繁见她一脸愣怔,贱兮兮地叹气:“没让何小姐实现扒皮拆骨的心愿,不好意思。”
“浑蛋!”
何风晚回过神,羞愤交加地猛扑过去,朝他抡起手臂,那发狠的神情似要和他你死我活地打一场。
却忘记经过刚才一番折腾,力气都耗尽了,才站起就是一阵大脑缺氧的眩晕袭来,她两眼发黑地往后倒。
江鹤繁伸手去捞,没想到被她拉着一起摔倒。
两人一道往坡下滚了几米。
何风晚睁眼,江鹤繁的脸近在咫尺,这才发现自己始终被他完好地护在怀里,半点没磕到。
他深眸温柔地一开一合,太近了,连剃净后泛青的须面,以及那些稀疏却长得不可思议的睫毛都看得清清楚楚。何风晚面向他的脖颈和脸颊烧起来,皮肤下血液亢奋地流动。
她推了推,没推动。
不得已,她喉咙挤出微弱的抗议:“你……”
江鹤繁这才松手。
顾不上数落,何风晚背向他脱掉手套,捂脸散热。毕竟顶着大红脸和他争执,实在太没气势。
却不经意瞄到他轻轻抖动的肩膀。
他居然在笑!
何风晚怒吼:“喂!你笑个鬼啦!”
江鹤繁随即缓了缓,说:“不是你让我笑的吗?”
“我——”何风晚简直气不打一处来,凶着脸,“我没让你现在笑!”
江鹤繁索性转身,似笑非笑地盯着她。
眼前的何风晚一张脸皱巴巴的,泪痕斑驳,看着惨极了。
她赶紧偏头,音量明显小下去:“看我干什么?”
“等你告诉我什么时候该笑。”
可恶!
何风晚气急败坏地大叫:“现在不许看!也不许笑!”
身后便真的没了动静。
及至情绪平复,之前萦绕在她心头的那点难过也散去了。
江鹤繁这才又开口:“这是小型的松雪塌陷。刚才那块积雪下藏有空间,我的滑动造成额外负载,坡面受力引发了塌陷。
“不过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还好运气不错。我冲过雪崩区,躲在岩石旁边观察有没有后续的塌陷。看着阳光不错,就顺便躺下,然后听到何小姐的声音。”
想起刚才的惊慌,何风晚生气地说:“没事就早点出来露个头很难吗?知不知道我真的以为……你这样叫别人担心真是……”
“让何小姐担心了。”江鹤繁诚恳地垂目。
他低眉顺眼地率先缴械,叫何风晚无措地张张嘴,仿佛再生气就是她的错。
算了,反正刚才摔倒的时候,他也帮了忙。
何风晚整顿行装,重新穿好雪板,漫不经心地说:“天晚了,我们回去吧。”
“好。”
返回缆车中转站的路上,两人各怀心事地沉默着,赶在太阳落山前,搭乘缆车去往预订的木屋,与其他人会合。
连排木屋建在山间,是当地人开设的小旅馆。
餐厅面积小,何风晚进去时,里面已经挤满了围桌而坐的游客。
长条餐桌铺有洁净的白色台布,杯盘刀叉一应齐备,雪白瓷盘里放着叠好的毛巾。两侧的角落各摆放着一盏瘦瘦高高的落地台灯,暖白色灯光寂静,如那个宽厚有力的怀抱,护人心安。
何风晚绾了一个松散的发髻,脱去外套,抚上温热的颈望向窗外,没去参与身旁哄哄的笑闹。
细柔光线自她头顶倾下,毛衣领口现出半边锁骨,弱不禁风的瘦。与她在雪坡上呼声震天的气势相去甚远,想不出那副身板还能爆发如此巨大的能量。
江鹤繁看了一阵,注意到成珠珠不时觑来的八卦目光,随即别过眼睛。
成珠珠被他发现,吓了一跳,哭丧着脸向何风晚求救:“晚晚,江江江……江总今天心情,他心情还不错吧?”
何风晚闻声看向江鹤繁,他正被林熊拽着闻酒味,拧着两道好看的眉毛,嘴角拉直,满脸的一言难尽。
何风晚不由得想起他的笑,想起被他抱在怀中时,她乱糟糟的脑子像往火中加氧,呼地蹿出冲天火舌,舔得她心底痒痒的。
何风晚点头:“看起来不错。”
成珠珠心有余悸地灌下几口啤酒,说:“今天林大哥临时有事,教了我一会儿就走了。我还没学会呢,好绝望啊!结果中午的时候,庞默来了,教得还不错,人也超有耐心!不过,他不是和你一起上山了吗?”
“本来和我一起,但是有些人不让。”何风晚笑着支起下巴,转向另一边。
与同时看来的江鹤繁视线相触,一瞬分开。
苍茫暮色于窗外半山合拢,山巅附着的皑皑白雪反着殷红的霞光。窗上贴有雪花图案的窗花,屋檐下围着长串的星星彩灯,灯影闪烁流溢。
江鹤繁与何风晚对那场小型雪崩,始终默契地缄口不谈。他们分坐长桌两侧,隔着重重人影,也未曾搭上一言半语。
但彼此的存在,前所未有的强烈。
像是一同叫了份鞑靼牛排,一同点了份密瓜沙拉,一同退出明天计划的巡山。因为留了心,所有巧合便顺理成章地隆重起来。
当众人还懵然不觉,他们已用被灯光烘暖的视线,在桌上肆意地互追互逐。
何风晚侧过头,手指轻抚拉长的颈线。她优雅的天鹅颈如濯净的细瓷,光照下尤其动人,可惜光线探不进领口,只留下一小片阴影,诱人坐立不安。
长眼倏尔一闪,她的眉梢,她的嘴角,她的指尖,柔情蜜一般流淌。
江鹤繁眼里的温度一点点抬升,很快受不住地移开目光。
想到他此前从没这样专注地看过哪个女人,没将她们放在眼里,总一副心冷如铁的样子,何风晚就无比快活。
一快活,她忍不住多喝了几杯。
后来被谁搀进房里的,何风晚不记得了。
凌晨四点,手机嗡嗡振动着将她拖出梦境,何风晚睁不开眼,锁着眉头想直接挂了它,却意外接通了。
“……喂?”她有气无力地哼一声。
“这么多天没联系,你不会真玩爽了吧?”线那头是孙道然。
何风晚顿时清醒了,低声嘟囔着“你等等”,掀开被子。
“我已经非常小心,尽量从他的话题导入,但他还是警觉地不愿多说。”二楼阳台风急,何风晚有些烦躁地踱步,裹紧了大衣,“而且他知道我有意接近他,叫他开口的概率就更小了。”
“他喜欢你吗?”
“……欸?”何风晚怔了怔,脚下一顿。
“当初说好了,我给你安排机会,让你尽早搭上他。你这么人见人爱,江鹤繁也不能例外吧?”孙道然干巴巴地笑,“等你拿到我想要的,我再给你你想要的,不是皆大欢喜吗?也不枉我栽培你这么多年。”
栽培?就买了一张机票,联系一家快倒闭的经纪公司,从此再没管过她,任她自生自灭。
直到去年她境况好转,他突然又来找她。
是没想到弃子又有了利用价值吧?
“我有说错吗?”似乎从她的沉默嗅到不服,孙道然帮她回忆,“我给你接那么多饭局,不能不算悉心照顾吧?你的事业,我也多有打点。”
“是啊!”何风晚扬声冷笑,“孙老板大恩大德我何风晚没齿难忘,你放心好了,我会尽力帮你查出那笔钱的下落。”
“哈哈,好。你也不用担心,老话说了,淹死的向来都是水性好的。就是知道你故意接近他,才会轻视你。”孙道然似乎在抽烟,传来轻微吐气的动静,忽然想起什么,嗤笑,“不过你可别自己栽进去了。”
何风晚翻翻白眼,转向背风处,咳嗽一声:“别小看我。”
“行,我不小看你。”孙道然悠然感叹,“我是真想看看,知道爱上的女人其实别有所图,他会有什么感觉?哈哈!”
“是啊,我也想看看,知道一直奉为上宾的兄弟无时无刻不在算计他,他会有什么感觉?”
孙道然没说话,迅速挂了线。
何风晚彻底醒了,回去一时睡不着,便站在阳台上远眺模糊的山影。
万籁俱寂,大衣下是她伶仃的脚踝,疾风吹起她的长发,细条条的人影有些凋零的意味。随风携来的湿凉细针一样,在她裸露的皮肤上留下细小的尖锐的疼痛。
“何小姐,早上好。”
江鹤繁走上相邻的阳台,看见何风晚,自然地同她打招呼。
何风晚见他精神抖擞的样子,有些吃惊地问:“江先生,你又这么早起?”
“习惯了,一向这么早。”
“那要是你以后的女朋友是夜猫子,不就和你有时差了吗?”
江鹤繁不咸不淡地看她一眼,没吭声。
嘁,还真是不好套话。
“那不打扰江先生观赏日出的雅兴。”何风晚打了个哈欠,佯装睡意来袭地揉眼,“刚才让珠珠的梦话吵醒了,起来吹吹风。我呀,和你可不一样,我就是夜猫子。”
语毕,她转身离去,没有看到江鹤繁注视她离去的身影时,抿唇笑了下。
回想雪山上,她咬牙切齿地叫他名字,远比单调的“江先生”生动。
女朋友?
他以后会有女朋友吗?
如果爱情让人快乐,那怎样才能不把每一次的快乐,视作一场罪过?
等何风晚走远,江鹤繁拨通楼焕的电话,问他对何风晚的调查。
楼焕说:“孙道然除了赞助何风晚去美国的机票,还为她联系了一家经纪公司,虽然没多久就倒闭了。头两年他们没有任何联系,直到去年才恢复见面。”
江鹤繁静静握着手机,半晌才问:“他们是那种关系吗?”
“先生……”楼焕讶然。以江鹤繁一贯的态度,是不屑于关注这种八卦的感情细节。
“不用紧张,我就看看他们的交情到了哪一步。”
楼焕松了口气,说:“看起来不像,孙道然的花边新闻一直没断过,与何风晚每次见面都很短暂,应该只是简单的资助人。”
江鹤繁又陷入了沉默。
许久,他轻叹:“我知道了。”
保存二维码在手淘打开